本帖最后由 王木木 于 2010-10-14 09:50 编辑

訂制筆袋筆簾送綠色經典文庫,本本都是經典,隨機送出~

《沙乡年鉴》一书对我国读者可能比较陌生,但在世界上声誉远播,影响极大,是一本拓宽道德研究范围,实现伦理观念变革的经典著作。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创造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他认为,新伦理学要求改变两个决定性的概念和规范:1,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一个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2,道德上"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赋予它们永续存在的权利。为此,他提出"大地共同体"概念。他说:"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
但是,现在人类还是以土地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角色出现。例如我们的自然利用,完全是经济主义的。它还是由经济私利完全统治着,不仅强调大地经济利用的可行性,并且认为永远具有经济利用的可行性。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然而,这种完全以经济私利为基础的大地利用是难以奏效和持久的。

《增长的极限》从1972年公开发表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年代里,在我们这个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大国,重新出版这本“旧书”,仍然有深远意义。这不仅因为这本书早已是名满全球的一块丰碑,而且因为这份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们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人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在实际行动上必须高度负责,切实解决,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避免在严重困境中越陷越深,为摆脱困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
书中的观念和论点,现在听来,不过是平凡的真理,但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对这种惊世骇俗的警告,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听不进去。现在,经过全球有识之士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取得了共识。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条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 
《只有一个地球》一书,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为这次大会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虽说是一份非正式报告,但却起了基调报告的作用,其中的许多观点被会议采纳,并写入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因此,本书是世界环境运动史上的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 本书的两位作者,芭芭拉·沃德是一位经济学家,勒内·杜博斯是一位生物学家,他们广博的知识背景使他们能够胜任编写本书这样的工作。不仅如此,正像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所说,他们还应该被看成是一项合作事业的创造性组织者,因为本书是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的。 书中不仅论及最明显的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环境问题。书中始终将环境与发展结合在一起论述,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作者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还应该注意到发达国家对抗污染设计和技术上的发展,对那些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法,通过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国内外新投资者采用这些技术……经过仔细的计划工作,当前的一部分工业增长可以绕过工业化污染的原始阶段,而把新工艺设备纳入最初的整体设计之中”。本书对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是在归纳、总结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新人口论》 经典不必多言。

1974年,美国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教育家巴里·康芒纳出版了他的生态学著作《封闭的循环》。在书中,巴里·芒康纳带领读者重新回到生物圈的基本循环。“这本书主要是想发现人类的哪些活动破坏了生命的循环,以及为什么破坏了它。”作者试图从环境危机追溯其生态压力以及在生产技术及科学层面上的错误,最后追溯到“驱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作者认为,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发明的动因,往往是单一追求生产效率,或单一的消费使用目的,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多少算够》一书,通过解释需求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艾伦·西恩·杜宁论证说,消费者社会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由于它自己和它的星球的未来可居住性的原因,所有的父母都想给他们的孩子一个较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由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空调、更多的预先包装好的冷冻食品以及更多的购物街组成。如果交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为了满足个人的食物、教育、充实的工作、居所和良好的健康状况的需要,他们的选择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将是多么的美好!这种情况只要我们消费者社会中的那些人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发生。
一些微弱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转变是可能的,80年代的炫耀性消费已经让位于一个对消费有较低期望的时代。另外,这也反映了许多国家所陷入的衰退,各地的民意测验显示的现状远远不尽人意,现在是走出消费误区、走向艾伦所说的持久文化运动的时候了。持久文化就是一个量入为出的社会;提取地球资源的利息而不是本金的社会;在友谊、家庭和有意义的工作之网中寻求充实的社会。正如艾伦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指出的那样,联系人类和自然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消费者的手中。

本书最早出版于1980年,探讨了科学革命如何认可了自然的开发、贸易的扩张以及女性的被奴役,塑造了20世纪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与过去数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之间强有力的关联,并对自然与生命的有机论和机械论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有洞察力的讨论,同时,在澄清妇女———自然的关系的复杂性方面本书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自然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问世,它向人类已经概念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挑战,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这一关系。
这本厚重的著作以丰富的资料描述了人们自然观的变迁,并对这种变迁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尽管我们素来推崇物质的作用,但从更宽泛意义上说,观念的确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自然观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它反映出人类界定的人与自然的概念,决定了人为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定位。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自然概念同性别概念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这并不是说让人否定现实中的人和树木,河流和植物,而是暗示了妇女和自然如何可以想象为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范畴,同性别概念一样,自然概念也是随着文化、历史以及时代发生变化的。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
自然作为有机体的观念在古代哲学中便可以找到根源。有机理论的核心是把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形象等同起来。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对人类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强制力,因为这一预设尽管表面看起来是对自然的一种规范性的陈述,但它承担起“应当”的道德负荷。当人类出于商业目的对有生命、有感觉的地球母亲进行残害时,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古代哲学中的这种自然有机论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成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它们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同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有的东西通过相互吸引和爱联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反映出宇宙其余部分的变化,世界各个部分的紧密联系不仅含有共同滋养和成长的意思,也包含共同承受痛苦的蕴涵。
然而,17世纪生态、商业、技术的发展催生出的一种机械论取代了“有机论”的自然观。这种观点把自然看成是死的、把质料看成是被动的,并且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这种机械论也构成近代西方文化试图驾驭自然、征服和统治的自然的理论根据。纵观历史,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之间的争论自“科学革命”以来便一直很有影响。
面对当前自然资源被耗尽的危机,西方社会又重新开始重视前机械论世界的环境价值,有机论为现代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的哲学框架。现代生态学扎根于有机论,麦茜特所倡导的生态女性主义也是如此,但是,她已经无意于重新确立起自然母亲的形象,让妇女继续接受由历史派定的养育者的角色,而是要考察妇女与自然相关联的价值,考察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对传统自然观的冲击,以粉碎旧世界的方式呼唤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对过去的新解释提供了透视现在的视角,并成为变革现实的力量。”
从女性主义角度评说历史便是从社会的最底层来审视社会结构,正因为这一革命来自社会结构的底层,因此也最具有颠覆性。《自然之死》要颠覆的是“科学革命”以来的主流价值观,揭开科学“父权制”神话的假定,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科学机械主义世界观一直都在行使对自然和女性的剥削,而且这种剥削正在导致一个活生生的自然存在的死去。麦茜特强调,机械主义使自然死亡了,把自然变成可从外部操纵的、惰性的存在;机械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事实上是一种概念化的权力结构,换句话说,机械主义世界观归根到底是由政治权力驱使的。麦茜特高举起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旗帜:即把对“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妇女解放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女性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
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顽固地持续下来。她们古老的相互关联已经被近来同时发生的两个社会运动所戏剧化,一个是妇女解放运动,由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神秘》这个有争议的雏形为其象征,一个是生态运动,它兴起于60年代,最终在1970年的地球日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公众对它们均采取一种平等主义的眼光。将这两个运动并排起来,可以看出新的价值和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建基于对妇女和自然的支配,而是建基于男性和女性才能的充分表现,建基于环境整体的完好保存。
16、17世纪之际,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自然之死》考虑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和科学上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这一巨大的转型。在试图理解人们是如何在“科学革命”中将自然概念化的,作者卡洛琳?麦茜特没有诉求不变的本质,而是诉求社会变化与变化着的自然建构之间的关联。类似的,当今的妇女试着改变社会对自然的支配时,她们是在推翻自然和妇女作为文化上被动的、次要的种种现代构建。在考察这一转变的时候,作者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科学内容的内在发展上,而是注重包含在这种转变之中的社会和思想的因素。当然,这些外在的因素并没有导致知识阶层为着有意识的目的,发明与社会境域相适应的一门科学或形而上学。
卡洛琳·麦茜特博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保护与资源研究系环境史、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教授。《国际妇女研究季刊》评价这本书是“一本博学之作……妇女-自然的关系昭示了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范式,本书在澄清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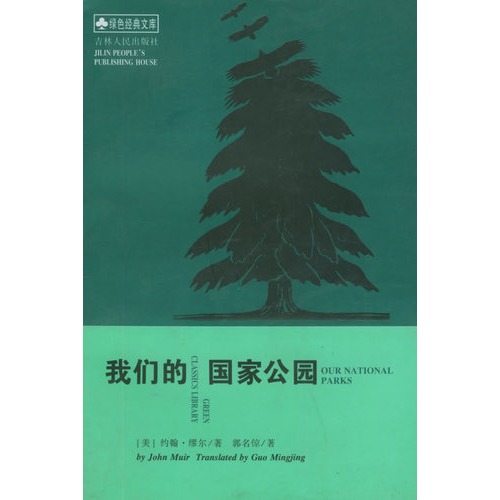
《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作者是著名的美国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约翰·缪尔。他只身踏美国万水千山,以亲知记录和描述了现已破殆尽的主要是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天成、感人至深的景象,其中折射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任何怀疑写作之威力的人,只要想想约翰·缪尔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深信不疑了。
——《美国读本》
以其对美国风景丰富但又时而文彩四射的描述,对植物、树木和岩石博学的编目,对自洪荒时代以来沧海桑田的直觉的再创造式的地理叙事,对《圣经》以及他所喜爱的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多次征引,缪尔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注意力。
——《环境主义者书架》
本书吸引读者的地方是:对多彩的自然风光浓墨重彩,有时是光芒四射的描写;提供的植物、树木和岩石的大信息量的名录、地质描述——从混沌初开到现代直观地再现了地质事件,以及对《圣经》和两位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黄故的多项引用。然而超出其他一切之上的事,本书不断持提醒我们对大自然的需求和我们对大自然的责任。
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我国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我们的国家公园》是一部至高无上的指南,是由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帮助创造的,对于约塞米蒂和其他那些了不起的公园的激动人心的展示。跟随约翰·缪尔快步穿行于国家公园之后,以往的旅游者想以新的视角重访故地,而不曾造访过的人则按捺不住向往之情。
这本长期绝版的书最早问世于1901年,在此之前,它的10篇美文就已先行见诸于《太平洋月报》。缪尔怀着一个单纯的企图来写作———用他的描绘吸引人们到公园来,看和欣赏。如果足够多的人追随缪尔而来,他们必然会像缪尔一样地热爱这自然美景,公园便可得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公园》有回想,有哲学,更多的是迷人的描述。
虽然书中介绍了黄石公园、红杉公园、大峡谷以及美国其他国家公园,但是缪尔赋予了最多的热情于他的最爱———约塞米蒂,深入内华达州塞拉的心脏。缪尔解释说:“在我攀登过的所有山脉中,我最喜欢内华达的塞拉,尽管它极度崎岖,它的主要面貌展开在最宏大的高度和深度之上,但并不难接近,并且热情好客,它那令人叹服的美丽展示出惊人的和迷人的形式,引来崇拜的游人络绎不绝,其魅力和魔力无穷。” | 